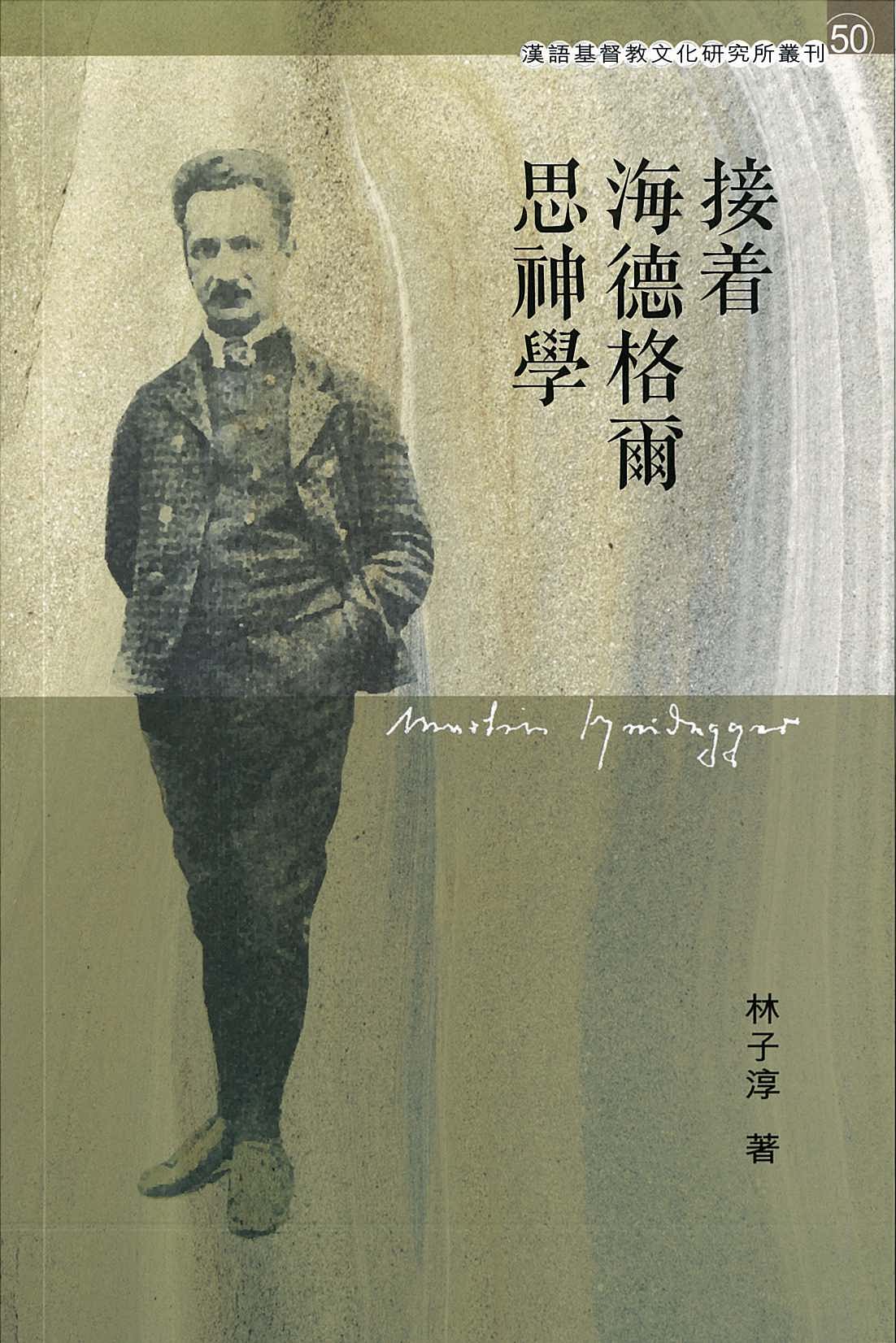
系列︰道風叢刊
編號︰ISCS-50
書名︰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作者:林子淳
ISBN︰978-988-8165-38-4
港幣售價︰$85
頁數:288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書籍簡介︰
神學在海德格爾思想中通常不被視為最核心的課題,然而年青的海德格爾確曾在致洛維特的書信中言及自己是一名「基督教神學家」,又對日本學人稱「沒有這一神學的來源我就決不會踏上思想的道路,而來源始終是未來。」
本書一定程度上是為這些話作注解,致力探索海德格爾思想與神學的淵源,讓哲學界對其有關基督宗教的論述有更好的把握,也讓神學界理解何以海德格爾的哲學會觸發這麼大的迴響。
然而若單接着海德格爾來講神學而不作批判,後果很可能是重現他在二戰時期所遭遇的困局,故我們還要反思究竟可怎樣吸納他、挪用他?海德格爾會否只是展現出一個常人在困逼時期的生存現象,是我們每個人的一面鏡子?
作者簡介
林子淳
現任澳洲墨爾本神學院基督教思想高級講師、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駐澳洲研究員、上海同濟大學兼任教授,研究範圍包括神學與哲學詮釋學、當代神學、神學處境化問題等,著作和編纂有《存在.歷史.神聖》、《敘事.傳統.信仰》、《利科:在聖經鏡像中尋索自我》、《哈貝馬斯的宗教觀及其反思》等。
目錄
孫周興 後神學的神思——序林子淳博士《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瞿旭彤 在哲學與神學「之間」—為子淳兄新作《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而寫的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形式指引的基督教底色
第二章 從路德回到保羅式的基督教
第三章 甚麼召喚神學?兩種可能性的檢視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從存在到神聖的尋索
第五章 海德格爾的「基督論」思考
第六章 四重整體與最後之神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神聖社群現象學的構想
第八章 榮耀意見的發生
第九章 技術追問與政治糾葛
詞彙對照表
後神學的神思——序林子淳博士《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林子淳博士讓我替他的《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作序,我深感幸運。作為同行和朋友,我跟子淳博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道,乃基於學術上的共同愛好和旨趣。
子淳博士多年來從事海德格爾與神學研究,成績斐然,是漢語學界難得的一位神學現象學家。自二○世紀八○年代以來,漢語學界對海德格爾思想的關注可謂熱烈,但要從基督神學的角度來研討海德格爾,難度絕對不小,因為研究者至少要兼通海德格爾與基督教神學。弄懂海德格爾思想已屬不易,加上神學,就難上加難了。我以為,子淳博士在此領域內的工作是最有貢獻的。
我們知道海德格爾的家庭背景是基督教神學。他本人原來也想投身於神學和神職。但在弗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神學系學習不久,接觸到哲學(存在學),便終止了這條主要由家庭背景決定的神學道路。可以想到這時候的海德格爾身上就出現了哲學與神學的糾纏。後來的海德格爾把形而上學設想為哲學與神學的雙重結構,並且認為兩者具有「互校」關係。
在歐洲歷史上,哲學與神學分屬兩個知識系統,哲學源自希臘傳統,而神學源自猶太希伯來傳統。這兩個系統的精神取向是大相徑庭的。我以為,就基本特質而言,哲學重論證,而神學重信仰—信仰也即服從。也可以說,哲學不信仰,而神學少論證。當哲學開始信仰時,哲學便進入僵化的教條;而當神學開始論證時,神學以及宗教離消亡不遠矣。
就個體而言,情形也差不多是這樣。我常說人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心力旺盛、心思強大的,習慣於自己掌握自己,自己來論證自己的念頭和行為,這種人適合於做哲學和讀哲學;而另一種人心思偏弱,願意服從,願意接受指引,願意把自己交出去,這種人適合於信教。千萬不要搞反了。搞反了是會有後果的,是會害神害己的。
然而,偏偏在歷史上哲學與宗教經常糾纏在一起,也偏偏有一種哲學叫「宗教哲學」。以個體信仰為重點的神學希望通過哲學的概念和方法,把神性之事說個清楚,也即給出一種哲學式論證,終致「上帝之死」。另一方面,哲學也總是躍躍欲試,夢想解決「個體無法言說」的持久難題,所以一直有「實存哲學」的暗潮湧動。可以看到,歷史上的「實存哲學」多半是有神學傾向的。
回到海德格爾來說,上述錯綜複雜的情況在他的思想進路中均有體現。且不論前期海德格爾的實存哲學所具有的神學動因,後期海德格爾以「神聖者」(das Heilige)和「最後之神」(der letzte Gott)的思想,終究也可歸於「後神學的神思」。我相信,有朝一日,人類將隨海德格爾重啟神思。
也許子淳博士已經開始了這種重啟。子淳博士的這本書(論文集)由三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均為三篇文章,第一部分涉及前期海德格爾與神學,第二部分討論後期海德格爾的神思,第三部分則希望從海德格爾出發思神性問題,是所謂「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我喜歡這樣的構造。
是為序。
孫周興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記於青島
在哲學與神學「之間」——為子淳兄新作《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而寫的序言
二○一八年秋,在明媚靜謐的普林斯頓小鎮,我安心閱讀着巴特(Karl Barth)。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子淳兄來信,希望我為其新作《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撰寫序言。出於我們多年交往的學人情誼,我不揣淺陋,欣然答應,同時也倍感榮幸與不安。故,如履薄冰,鄭重其事,望不負所托。
二○○六年夏,我第一次造訪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道風山開元居逗留兩個月,與子淳兄結識。自此,我們時有互動交流。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我與輔仁大學哲學系曾慶豹教授聯合主持第一屆「北師大-輔仁漢語哲學與神學工作坊」,邀請子淳兄和胡繼華教授一同閱讀和研討海德格爾早年重要作品《宗教生活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借着這樣帶有學人共同體性質的工作坊、以及與此搭配的系列講座,我們想要在漢語學界持續推介對哲學與神學關係的理解和研究,加強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拓展與提升學生對相關問題的視野與興趣。子淳兄當時負責領讀其中一部分,此書第一章即源於此。後來,慶豹兄受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學刊》編輯部委託,以工作坊領讀報告為基礎,主持相應專欄。在四位作者和編輯部同仁的郵件交流中,我專門就子淳兄相關文章關於亞里士多德的部分寫過幾句點評。子淳兄對這些點評似乎頗為滿意,因而才發動了想請我撰寫此序的念頭吧。
於我而言,神學和哲學均是個人的興趣和激情所在。一九九四年,我開始學習哲學,在先前的海德格爾研究重鎮做過多年學生。二○○三年,我開始進修神學,逐漸專注於巴特的神學思想。二○○八年,導師和一位剛博士畢業不久的教席同事主持關於《宗教生活現象學》的密集研討班,專門研討海德格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關於保羅和奧古斯丁的詮釋。由於海德格爾對保羅的闡發,更由於海德格爾與巴特在時代精神與具體思想上的平行性與相似性,我借此研討班,真正開始進入海德格爾的思想世界。在我看來,巴特和海德格爾的諸多作品均圍繞各自思想實事展開,因而成為各自思想道路的一座座路標。巴特一生的神學思想旨歸是見證和指向神學的實事,即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啟示。而海德格爾一生的哲學思想旨歸則是指向哲學的實事,即存在和存在者之間彼此互動、互相歸屬的複雜關聯(我在此想特別提及,胡塞爾(Edmund Husserl)現象學的口號是「我們想要回到實事們本身」[Wir wollen auf die Sachen selbst zurückgehen],而海德格爾提倡的則是「朝向思想的實事」[zur Sache des Denkens]。前者強調「我們」,且「實事」為複數,有主體主義的嫌疑;而後者力圖克服主體主義,因為對思想所指向的實事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按傳統形而上學語言描述,兩者均關注「一與多」或「同一與差異」的根本問題。巴特作為一位神學家,將「多中之一」落實於特殊且具體的耶穌基督,這是其神學形而上學的核心和原則。而海德格爾作為一位哲學家,將「多中之一」歸結於不斷彰顯和遮蔽自身的存在者整體,這是其哲學形而上學的指向和歸宿。就此而言,這兩位思想家均致力反抗近現代強調上帝內在性的主體主義思想傳統(比如,康德所謂「在我們心中的上帝」[Gott in uns]和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並試圖為個體性的多和實質性的差異爭取本體論地位。在這般反抗中,兩者思想的起點均是康德批判哲學對人類理性認知能力的限定。因而,兩者並不試圖如同黑格爾或謝林(F. W. J. Schelling)那樣回到強調萬物源初同一的古典形而上學,而是堅定地從多和差異出發,並努力指向那已來又將來的一,並不自以為已達臻與智慧為友的神人同一境地(「自我神化」)。
正是憑着這樣對海德格爾的「粗闊」理解,我開始閱讀子淳兄大作,有許多得着和莫大收穫。子淳兄大作共分三大部分,每部分各三章,共九章,前後再加以前言和結語。整部作品猶如美妙的音樂織體,結構清晰,節奏明朗,韻律新穎,蘊涵雋永。
第一部分着重處理海德格爾早期作品的基督教思想來源(Herkunft)或「神學維度」,並試圖回答青年海德格爾為甚麼會自稱為基督教神學家。在此,子淳兄呼籲,「在研究海德格爾思想時,我們或許應更關注其早期思想,尤其與中世紀神學的關聯」。[1]他還特別提及馬丁.路德在中世紀晚期大背景下提出十字架神學的重要意義:「路德的信靠乃出於其十架神學,也看作一種經驗神學[……]必須從此世中的十字架事件作起始,而非對一位無形上帝形象的玄思。這正是引導海德格爾為甚麼要回溯至早期基督教信仰的原因」。[2]我非常認同子淳兄的這一敏銳觀察。在我看來,海德格爾所承繼的、強調神人差異、強調個體經驗和生存歷史的路德十字架神學進路,至少可追溯至中世紀晚期唯名論對唯實論的反抗。唯名論與唯實論的分野堪稱理解近現代思想(特別是其形而上學和上帝觀)的根本出發點。在以唯實論為代表的亞里士多德-托馬斯形而上學傳統中,人之所以能夠認識上帝及其所創造的世界和自然秩序,乃是因為上帝的第一屬性是理性,他對世界的創造首先是出於他的理性。由此,人可以通過合理世界之果,由果推因,通過存在鏈條的逐漸上升認識上帝、及其創造世界的目的。而在以唯名論為代表的近現代形而上學傳統中,上帝的第一屬性是意志(愛),他對世界的創造首先是出於他愛的自由意志。由此,世界與上帝之間的因果關係和存在鏈條被徹底斬斷,人與世界的存在成為偶發的,而並非必然的,因而是值得驚異的(參維特根斯坦的相關名言)。相應而言,傳統形而上學對上帝的理解是從上帝的本質(Sein)及其屬性(上帝是甚麼)推導出上帝的行為(上帝如何行動)(本質先於存在),而現代形而上學則試圖從上帝的行為來理解上帝的本質(存在先於本質)。就此觀之,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顯然屬於後一種形而上學傳統,強調如何先於甚麼、存在先於本質、動詞先於名詞、動態先於靜態。與此同時,海德格爾又試圖拒絕和反抗同樣源自唯名論的現代主體主義傳統。
早在《宗教生活現象學》一書中,海德格爾憑藉對歷史問題這一人類基本生存經驗和核心現象的關注,已揭示出他關注差異和源初經驗、並試圖對哲學實事作出形式指引的基本思想特質。正如子淳兄所言,海德格爾早期思想並非「過於幼嫩和未具系統性,對後來的發展不一定有多大意義」,而是「與後來的重要概念有極大關係」,因而不能忽略其思想來源處的「基督教神學底色」。[3]由此重要觀察出發,子淳兄不僅成功凸顯出海德格爾早期思想及其基督教神學底色對其思想道路(特別對《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而言)的構建性意義,並進而認為,海德格爾在後來「仿似仍延續着他早年已開始着的思想旅程,個中似乎沒有甚麼思想『方向』上的轉向(Kehre)」。[4]筆者認同子淳兄這一看法。如前所說,海德格爾思想走的確實是同一條指向同一哲學實事的思想道路。他不僅尊重個體生命源初的、歷史性的、充滿活力的生命經驗,而且強調存在者整體彼此互動、互相歸屬的複雜關聯。這是海德格爾從生存論角度對古典形而上學同一與差異這一經典問題極具現代性的解讀與回應。就此而言,無論是早期,還是中期,還是晚期,海德格爾不同時期的諸多作品都只是這同一條思想道路上的不同路標(Werke als Weg)。《存在與時間》或許是海德格爾思想道路上最為人所知、且影響最巨的路標,但它也僅是其中一座路標。海德格爾早期思想的創造性、多樣性和複雜性絕非單單指向《存在與時間》、並以之為歸宿與終結,而是標誌着和呈現出其思想發展道路上可能蘊含和湧現的諸多豐富可能性,例如,與中世紀哲學和基督教神學千絲萬縷的緊密關聯。
關於這樣的緊密關聯,我舉子淳兄大作中一例稍作說明。子淳兄曾特別提及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和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解讀亞里士多德上的差異:「正因要把對個體存在物的前理論體驗跟範疇直觀接連,司各脫和托馬斯.阿奎那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之分別是關鍵的。司各脫聲稱自己是位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卻不接受被認識者的普遍性和被經驗者的個體性是分離的,並以為個別的感性經驗在智性活動以先已是可理解的,明確地反對阿奎那的想法。換句話說,若沒有對個體的一些先前知識,根本就不可能從中抽象或概括出普遍性來;抽象出來的並非原初知識,反倒預設了智性的更基本經驗。因此,個體是本質地而非意外地個別化的,思想從一開始便與存在(essentia)有關,這才使得事物成為可理解的;而並非如阿奎那所設想,僅透過思考者的智性中介所作用。」[5]在之前提到的郵件交流中,我曾做過如下相關點評:就我個人五年以來對亞里士多德的教學和研讀經驗而言,從海德格爾思想強調差異、個體經驗和生存歷史的現代立場出發,我們可以推斷,海德格爾會極為贊同司各脫的解釋,而反對阿奎那的柏拉圖化理解。在我看來,首先,亞里士多德常被提及的形質說和實際上更為根底與關鍵的潛能-現實說,恰恰是在反對被認識者的普遍性、及其與被經驗者的本質分離,而這種分離是柏拉圖外在理念論所主張的、亞里士多德內在理念論(即形式說)試圖克服的。海德格爾講的可能性(不僅僅是可能性,而且是能力)恰恰是對亞里士多德潛能-現實學說的顛倒:潛能高於現實,將來先於過去。而海德格爾之所以能如此行,不僅是因為以往中世紀晚期唯名論對唯實論的反抗,也不僅是某些學者所以為的來自謝林思想的影響,更是因為其自身思想的「基督教神學底色」,即對以將來為導向的保羅終末論的形式化重構與闡發。其次,就思想與存在的關聯而言,思想與存在不僅一開始就是彼此關聯的,而且是相互同一的。也就是說,人的理智的邏各斯和存在的邏各斯是同一的,這是人之所以能夠認識存在及其本質的古典形而上學前提。就此而言,海德格爾思想是對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問題(特別是分離問題)在後現代語境中的更新、甚至復興。但是,由於所承繼的唯名論傳統和十字架神學根底,海德格爾不再強調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思想與存在的同一,而是以存在與存在者的本體論差異為出發點,強調彼此作用和互相歸屬的存在者整體。由於存在者整體自行運作的彰顯和遮蔽,作為此在的人不能完全地認識這一整體,但可因循神聖者留下的些許蹤跡,形式地指向這一整體。不過,有徹底反對差異和後現代的學者可能會指出,海德格爾這樣對古典形而上學的更新或復興恰恰是在根底上取消了古典形而上學,因為他對差異和生存的強調正正否定了古典形而上學對同一(並非有所差異的整體)的堅持。或許,我們也可以從此角度理解劉小楓先生的海德格爾批判(下文將有所涉及)。
子淳兄大作第二部分以《哲學論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為核心文本和關鍵之作,主要追問海德格爾如何和為甚麼從三十年代起放棄他對早期基督教的興趣、而轉向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和尼采的「新神話學」。由此出發,子淳兄開始從神學角度反思海德格爾作品中重複出現的「上帝」、「神性」和「神聖[者]」等觀念,進而認為,海德格爾的「最後之神」具有強烈的基督論關懷,並可能受到神學家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和哲學家謝林的影響。對專研巴特思想的我來說,子淳兄令人驚喜地(雖未明言地)呈現出巴特與海德格爾思想的一些平行與相似特徵(這是我在之前有所感覺、但並未明晰的)。例如,上帝並不是在自身的上帝,而是為了我們的上帝;上帝掠過我們的時間和歷史,上帝的啟示是歷史的,而歷史是我們可查見上帝蹤跡的唯一視域;啟示是「神聖突入」的偶發事件(Ereignis,子淳兄沿用孫周興先生譯法「本有」。在我看來,這一拒絕因果必然性、反對現代主體主義、極具後現代色彩、因而強調差異、動態和偶發的用詞其實源自生物進化論中的突變[mutation]概念,並對應於近來流行的湧現[emergence]概念);上帝在啟示中是自主的,並不是主體之「我」的客體。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正是因為如此這般的平行與相似,在「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的路途中,特別是「關係到亞洲甚或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時,巴特神學與海德格爾哲學在強調垂直超越的恩典或禮物維度、反對現代主體主義、拒絕回歸古典源初同一的思想道路上的互相比較與彼此生發,或許是值得相關漢語學人奮力推進的一重要方向。
子淳兄在大作第三部分試圖從「一個神學家的角度」,讓海德格爾進入「公共學術平台」,與不同學科的不同思想家進行對話。在第七章中,子淳兄借助黑爾德(Klaus Held)和希恩(Thomas Sheehan)在闡述現象學實事本身時關於世界及其共同開放之政治維度的研討,批判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時期抗拒「意見爭論」而對公共性的共在世界所做的「非本真性」貶低,表彰海德格爾《哲學論稿》時期為抵抗「自我神化」而對共在整體和超越維度所做的刻意強調。由此出發,子淳兄針對「此世裏的社群政治維度」,取道神學家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提出「神聖社群現象學的構想」。在第九章中,子淳兄關注海德格爾與現代科技這一重要課題,並將之最終落實為對一切權謀造作的謹慎對待、以及對真理召喚的聆聽與參與。在第八章中,子淳兄論及「榮耀意見的發生」。在我看來,這一章可能是子淳兄全書最為精彩、也最為值得閱讀的一章。子淳兄首先援引希伯來聖經和希臘文獻關於(上帝的)榮耀和(本己的)意見(兩詞希臘文均為doxa)的思想資源,引出海德格爾思想承繼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從意見出發對公共世界所做的政治哲學探討。由此出發,子淳兄不僅試圖接着海德格爾進行深刻的神學思考,而且想要捍衛和更新對多與差異的現代堅持,為現代民主政治給出具有神學實質內容的批判性闡明。以對「在基督裏」的生存論分析為基礎,子淳兄認為,上帝的榮耀已然彰顯,人的意見及其決斷始終是不確定的。「故此,吾人在此世中只能不斷處於靠賴上帝啟示與對他者負責的辯證過程中。」[6]這樣的始終在路上的思想立場與態度,帶有鮮明的朝聖神學特質,其實也是海德格爾和巴特思想平行性與相似性的具體體現之一。
特別與第八章內容相關的是,為了準備撰寫此序,我專門通讀了劉小楓先生新近出版的《海德格爾與中國:與韓潮的〈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一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作為漢語神學運動最具影響的開創者和思想者,劉小楓先生曾任職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多年,算得上是子淳兄的同仁與前任。劉小楓先生新作是一部立場堅決、觀點鮮明、觀察細緻、論述精湛的專門著作,也是每一位海德格爾愛好者,特別是致力於關聯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漢語學人,應當通讀的思想佳品。劉小楓借着解讀和闡發韓潮先生的《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書(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批判現代性及其歷史主義和激進民主立場,特別是海德格爾精神後學阿倫特和劍橋學派所代表的立場。由此,小楓先生「寧可跟隨施特勞斯犯錯,也不跟隨海德格爾一起正確」,試圖回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永恆自然秩序」。有意思的是,這樣的「永恆自然秩序」恰恰正是子淳兄大作第八章所大力批判的,儘管子淳兄並沒有提到過劉小楓先生的這部作品。儘管他和劉小楓先生都非常重視現代性已經出現和可能產生的種種問題,但他強調上帝啟示恩典的垂直維度,而劉小楓先生則強調永恆自然秩序和具體靈魂差等的平面維度。在我看來,這裏體現出來的不僅是在中西之辯之背後更為根本與關鍵的古今之辯,更是在神人關係視域下對垂直維度與平面維度、以及恩典與自然之間關係迥然不同的立場與理解(就劉小楓先生漢語神學提議從垂直維度到平面維度的思想立場變化,我專門撰寫過一篇相關文章〈尼采以後—今天我們如何做漢語神學?〉)。[7]由此,若能將子淳兄大作和劉小楓先生近著對照閱讀,將是關心海德格爾與中國、海德格爾思想與漢語神學運動的學人進一步學習與思考、並且批判性反思自身所可能身處思想「洞穴」和神學「部落」的絕佳機遇。
二○一八年十二月初,經俊杰兄張羅,我與子淳兄再次幸會於雪後的西子湖畔。把水言歡之際,得知子淳兄即將離開工作多年的道風山,遠赴澳洲,加盟墨爾本神學院,負責系統神學教席,並且繼續推進漢語神學的思考與發展。特此祝賀,願他遠行順利,來日再相見!
是為序。
瞿旭彤
二○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醞釀和寫作
初稿於二○一八年聖誕節第一天
定稿於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 見本書,頁52。
[2]. 同上,頁42。
[3]. 同上,頁36。
[4]. 同上,頁54。
[5]. 同上,頁39-40。
[6]. 同上,頁239。
[7].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50(2019),頁155-182。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