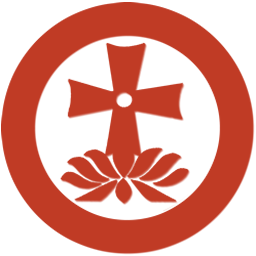作者:梅谦立(Thierry Meynard)
http://philosophy.sysu.edu.cn/introduc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82
从福柯(Michel Foucault)以来,西方当代哲学非常注意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其实,在他之前,古代的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语言本身包含着一种权力。从古希腊开始,正是这一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认识造就了修辞学这门学科。晚明来华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意识到,要获得中国人对自己所传播之事物的认同,必须运用修辞学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实,自西方传教士入华,便十分注意自身工作的策略,例如以传播科学知识为方式的策略,对此的研究已有许多,但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策略,例如我们将要在这里介绍的文体策略。我们的分析以《达道纪言》(1636年)为个案,这本书可算是中西合璧,一方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1566-1640年),一方是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约1596-1649年)。 就内容而言,这本书是一些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自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6条。就体裁而言,它以中国伦理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为五类,在这五类(伦)中,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朋友(122条)。再次是家庭伦理:父子21条,兄弟31条,夫妇23条。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易读,它的内容不是我分析的重点,我想要弄清楚的是,作者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进行编排,这种体裁考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进入这本书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认识一下西方修辞学的基本概念和作用。在第二部分,我将对修辞学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变作一介绍。第三,我会讲到,这些最早来华的泰西人,他们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一种修辞学尝试。最后,在第四和第五部分,我想表明,高一志和韩云如何希望通过修辞学来达到一种教育的目的,并试图形立一个话语团体。
一、修辞学与《达道纪言》
修辞学就是运用一种语言技艺来说服他人,它的第一阶段是累积具有权威的言语,明白它们的涵义,并记住它们,从而使它们成为一种语文储备,以便将来发言时能恰当地加以运用。为此,古代人搜集这些言论,并编成专门的书。在古代西方,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修辞学家之一布鲁塔克(在《达道纪言》里译成“布路大”,Plutarch,约45-125年)。他用希腊文写了两套书:《伦理道理》(Moralia)和《传》(Vitae)。除了布鲁塔克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到比布鲁塔克早一点的瓦勒流(Valerius Maximus,约公元前20-50年);他用拉丁文写了《值得记忆的言论和事件•九本》(Factorum ac dictorum memorabilium libri IX)。后来,还有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第二世纪)用希腊文章撰写的《名哲言行录》(Vitae Philosophorum) 。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作家搜集这些言论,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具有历史客观性的档案,而是因为这些语言材料包含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伦常纲要。换言之,这些言论提供一些道德榜样,使人们通过学习来趋善避恶。
在文学里,我们可以区分“记言”和“记事”。“记言”(格言或箴言),希腊文apophthegmata (άποφθέγυεσθαι), 拉丁文 dicta或sententia, 英文 apophthegms,是一些包含重要道理的语录;这些语录与谚语不同。谚语或古语属于大众传下来的智慧,而“记言”则联系到某个具有权威的历史人物。另外,记事,拉丁文facta,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某种行为或态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我们能找到有同样的区分:记录言论当为“记言”,比如《左传》、《尚书》、《国语》;而记录事件当作为“记事”,比如《春秋》。
在《达道纪言》中,“纪言”虽不是“记录”的“记”,而是用丝字旁的“纪”。可是,这个字跟“记录”的“记”相通。对此我们可以在序言中看到,“手纪”即“手记”:
西先生来宾,如大樽置衢,过者酌焉。始于吾师徐文定公,迄吾辈未艾也。大约西学规范严,一字之差,斥为异端,书三经审定,始敢传布。此书则则圣高先生时以语余,余手纪之者。
因为在这里“纪”等于“记”,所以我们有理由把《达道纪言》这本书的标题理解为《达道记言》。而且,大部分的条文有同样的结构:第一部分描述一个伦理问题;第二部分描述一个作为历史人物的古代圣人,他如何用言语来回应并解决这个问题。比如:
16 昔一府感王恩,立祠祀之,有美树生于祠,民媚王以为祥,王智不纳其媚,曰:“是树之生我祠,非益我之祥也;惟尔辈不踵是地之明效。”
He [Tiberius] forbade the voting of temples, flamens, and priests in his honor, and even the setting up of statues and busts without his permission.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Tiberius, XXVI, Vol. I, p 333]
这条“纪言”没有明确地提出国王之名。可是,因为前一条谈到了弟伯略王(Tiberius),所以这条也应该涉及到同一个皇帝。我们能在著名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里找到这个故事。可是,在“原初故事”和“最后故事”之间,我们应该注意其中存在着一个转化的过程。先是最初的“纪事”,它很简略地记录弟伯略王,说若没有他的许可,不得改建用他名字的庙。修辞学把这个“记事”当作一个语言的基本材料,使学生去进一步编故事。在希腊文里面,这样的材料称为“chreia”(χρεία),意思是说“可使用的”。台湾学者李奭学将此词译为“世说”。后人可以通过这一原初的基本材料,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进行补充和扩大故事的处境,意思等等。比如,上面的这个“纪事”就经过了类似的转变。在欧洲文学里,这个“最后故事”可能已经存在。但更有可能的是,高一志和韩云自己改编了故事,加上故事的处境(祠、美树)和机会(弟伯略王拜访这个祠)。而且,这个故事从“纪事”变成一个“纪言”。于是在中文包含了一种伦理判断:本来,美树是以自己的内在功能生长的。但是,这些地方的人的意志并不纯粹,不依靠自己的内在功德,而要用手段来得到外在的好处。他们种树,并不是为了国王,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这些chreiai是修辞学预备练习(progymnasmata, προγυμνάσματα)的很重要部分。在课堂上,老师提供一些“纪事”或“纪言”,让学生们去自己改编这些故事。
虽然如此,在《达道纪言》中,我发现只有两条纯粹的“记事”。下面属于君臣部分的一条:
131 历山王于老骥蓄而逸之,非阵不用;国有老臣,既用之久,宜待之优,而非大事不必劳之。
Once upon a time Philoneicus the Thessalian brought Bucephalas, offering to sell him to Philip for thirteen talents, and they went down into the plain to try the horse, who appeared to be savage and altogether intractable, neither allowing any one to mount him, nor heeding the voice of any of Philips attendants, but rearing up against all of them. Then Philip was vexed and ordered the horse to be led away, believing him to be altogether wild and unbroken; but Alexander, who was near by, said: “What a horse they are losing, because, for lack of skill and courage, they cannot manage him!”
这条文描述的是一个故事,但并不紧随着一个明显的“纪言”。可是,这条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类似于针对读者的言论。可以说,《达道纪言》几乎所有条文都是“记言”。这点代表这本书的性质:修辞学通过一些基本材料使学生们掌握历史中的著名言论,好使他们在将来发言时运用。这样的培训对后来欧洲耶稣会的教育法产生了影响。在欧洲的耶稣会学校,老师每天安排一些讲演比赛,围绕一个命题,学生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互相辩难。除了内容之外,培养的主要目的在于学生的说服力,在这一环节中,学生能否采用具有权威性的“纪言”占很大的作用。
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纪言”本身并不直接就是一种伦理学理论。在《达道纪言》上,这种伦理理论当然存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stoicism),但它隐含在语言的叙述之中,对于叙述可能具有的伦理意义,作者经常不直接解释或拥护。而且,条文之间时有矛盾,这是因为“纪言”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直接的普遍真理,而应是一种具有处境性的真理。我们可以说,这种修辞性言论所考虑的,首先是如何让读者在这样的一种阅读中觉得,其中的伦理意义是自己得出的,因此这些言论在他看来并不是一种外在律令,而是自己的内心发现。另外的一种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如此发现的意义是一种处境性的意义,从而具有一种当前实践的价值。
二、修辞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我们都知道,在基督教古代时期和中世纪,修辞学变成传福音的重要工具。从圣经或教父文学里面,基督教作家抽出一些容易记忆的语录,使基督徒记在心中。在中世纪,作家们也从圣经里面选出一些故事来,说明神学概念或永恒生活的道理。这些具有说服力的故事被称为“比喻故事”或“证道故事”(exemplum)。从12世纪起,这些语言材料被搜集,并汇成书册,以帮助神父们准备讲道之用。 这些书用希腊文说就是anthologia或拉丁文florilegia,意思是“花束”。读者能自由地采摘一朵。这些内容,按逻辑次序(比如,神学美德,基本美德)或按照拼音次序排列。 那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材料用得并不多,即使用,它们也往往被用来表达一些神学道理。
可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是印刷业的发展。在中世纪,人们读书时,因为书太大太重,无法携带,所以应该尽量把内容背下来。在16世纪,书变得比较便宜,大众化,比较容易携带,所以没有必要记住书中的内容。而且,由于书不断地增加,一个人无法面对庞大的知识,需要提供一种新型的书,这就是摘记簿(locorum communorum liber,commonplace book) 。这些工具书提供一种一般性知识,使学生很容易选择他所需要的讯息,进而整理它们。这些工具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代替记忆力(修辞学主要依靠记忆力),而就是为了减轻记忆力的劳苦。在修辞学方面,第16-17世纪,好几百本类似的书面世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方面的第二个现象是要回归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修辞学的书那时还用很多圣经和教父们的“比喻故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逐渐吸收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更重要的是,希腊罗马的故事慢慢地独立于基督宗教的诠释: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很重要的道理,并不需要添上多余的神学诠释。因此,带神学色彩的“比喻故事”减少了,而接近原文的“纪言”则增加了。大部分作家都试图模仿布鲁塔克和瓦勒流。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爱拉斯谟(Erasmus),他出版了两本书:Adagiorum Opus(1528)和Apophtegmatum Opus(1532)。
第三个现象是,人们并不必需要用拉丁文,白话文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鲁塔克的书很快被译成了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也很自然地参与了这样的翻译工作,把古希腊拉丁文学译成中文。有趣的是,1579年,布鲁塔克作品被Thomas North翻译成英文,对莎士比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几乎与此同时,高一志和韩云把布鲁塔克的文集编译成了《达道纪言》。很少人注意到,英国人和中国人同时都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读古希腊拉丁文学了!
耶稣会特别重视修辞学。虽然哲学和神学作为耶稣会教育的最高层面,但实际上,他们同样花很大的努力来学修辞学。神学和哲学知识常常就是通过一些修辞学练习而得到的。当然,修辞学包括作文、言论两方面。 耶稣会士苏瑞芝(Cypriano Soarez,1524-1593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所编的《修辞学的艺术》(De arte rhetorica)成了耶稣会教育的常用教材,里面描述“修辞五步骤”:题材(inventio)、布局(dispositio)、文题(elocutio)、记忆(memoria)和诵说(actio)。 如此,除了思想的正确性,培养非常关注个人的表达能力,说服他人的能力。
三、传教与修辞学
耶稣会士们很快就对中国文化具有的高度有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对中国人,不能采用对非洲人和南美洲人一样的方法。刚好,欧洲的文艺复兴给传教士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们形成对人文主义的兴趣。在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试图加入中国文化的主流。因此,他们对非基督徒写了不少著作。很多这样的书不提神学的问题,它要推动的是一种“智慧文学”。 对耶稣会士来说,文化对话是一种必要的预备阶段(preparatio evangelica),目的是将来运用一种对话性的语言和思想来宣传福音真理。
传教士很快发现,因为他们自己数量很有限制,所以在中国传西方文化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而且,传教士可以自己发言,也可以著书。可是,怎么能保证听众或读者能真正地消化这种新食粮,而影响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呢。其实,为了提供传播的效率,耶稣会士自己依赖一些记忆术来学中文,吸收中国文化的庞大知识。他们也写了一些论文专门来介绍这些技艺,如记忆法。而跟记忆法有密切关系的是修辞学。到中国后,耶稣会传教士明白,为了广泛传播西方文化,修辞学能作为很恰当的传播媒介。为此,他们从欧洲带来了大量的西文书,包括修辞学的工具书。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我们还能看得到这些书,如Andre de Resende (1500-1573)所写的《记言与比喻故事》(Sententiae et Exempla)。 利玛窦从这本书中选择了一些“纪言”,而编了《交友论》(1595年),还写了《二十五言》(1605年)、《畸人十篇》(1608年)。
利玛窦认为,中国文化在文学方面很丰富,可是在演说术上有缺欠。为此,来华的耶稣会士,如艾儒略(1582-1649)在《西学凡》(1623年)中对修辞学做了初步的介绍。那时,他把rhetorica译成“勒鐸里加。”
高一志继续了耶稣会的汉语修辞学,在《达道纪言》中试图提供比《交友论》更大规模的西方伦理学。《达道纪言》完全属于这种宗教之外的人文主义文学。即使我们能找到几个天主教圣人,如奥古斯丁(Agustin)、耶柔米(Jerome),其实,其中令我们不解的是,作为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却不提到天主,而将该书的内容严格限制于伦理学内。
下面有很明显的根据:
77 彼里你阿曰:“金碙至坚,以羔羊之血泽之可碎。”人之强傲,以恩惠之情感之可服。
Now with reference to those affinities and repugnances which exist between certain objects, known to the Greeks as "sympathia" and "antipathia," phænomena to which we have endeavoured to draw attention throughout these books, they nowhere manifest themselves with greater distinctness than here. This indomitable power, in fact, which sets at nought the two most violent agents in Nature, fire, namely, and iron, is made to yield before the blood of a he-goat. The blood, however must be no otherwise than fresh and warm; the stone, too, must be well steeped in it, and then subjected to repeated blows: and even then, it is apt to break both anvils and hammers of iron, if they are not of the very finest temper. [Pliny the Elder, The Natural History, Book XXXVII, Chapter 15]
在欧洲,老普林尼(《达道纪言》译成彼里你阿Pliny the Elder)所描述的自然事实是很多欧洲人熟悉的。但教父却把这个自然故事当作基督之血的一个“比喻”:耶稣被称“天主的羔羊”(Agnus Dei),而他的血能够破碎最大的罪恶,如羊血能破碎金刚。 显然,《达道纪言》把这一自然事实转化成一种伦理上的道理,但却没有提供神学的传统诠释。
在西方文化中,不管发言或作文,运用“纪言”会带来很强的说服力。一提到过去的著名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王或恺撒,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马上被调动起来,而乐于接纳论点。“纪言”帮助确定个人和团体的身份。Scanlon指明,在身份成长和语言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他说:“自我以担任主体空位来成为自我。主体空位被意识形态或语言系统所创造的。同时,所有类似系统被断定于主体的外在存在来推动他们,不像形成好、独立的自我,而像他们所进的系统之外有外在动机的活动者。” “纪言”期待人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历史人物的位置,采用同样的伦理态度。这是一种行为性话语,为个人和团体树立一种伦理权威。
《达道纪言》大部分条文提到的历史人物有名有姓。在《达道纪言》中,计有约90个西人名字。从西方语境转到中国语境,这些“纪言”还能对中国人保持它们的语言作用吗?汉尼拔将军(Hannibal),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大流士(Darius)等在西方是些熟悉的名字,对中国人的耳朵来说,这些名字一定有陌生的感觉。这些西方历史人物没有被详细地介绍,中国读者无法知道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在西方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承认,因为缺少历史的背景,这些“纪言”并不能获得最好的修辞学效用。可是,有一些历史人物常常出现,比如亚历山大(14条)、他的父亲斐礼伯(10条)等等,那情况就不会一样了。我们知道,重复也是修辞学的一个技艺,它起码证明,这些就是西人心目中的古代君子。与中国的先王如尧、舜作为儒家的道德榜样,这些西方的古王也给西人提供了类似的榜样。高一志和韩云介绍这些“纪言”,正是为了使它们能进入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在晚明时开始,结果,亚历山大渐为中国人熟悉。
四、高一志的教育思想
高一志可算是一个教育家。实际上,他在意大利先教了五年的修辞学,后教三年哲学。 来华之后,他不仅试图写书,更考虑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材料和新的教育方法,来传播西学。因此,高一志跟中国人合作写了一套伦理教材,作这种新教育的尝试。他系统地编过:专门讨论儿童教育的一本书(《童幼教育》,1632)。于1635年,又按照“大学”的结构,写了三部著作:《修身西学》(ethica)、《齐家西学》(oeconomica)、《治平西学》(politica)。在这些著作中,他引用了很多西方的古代“纪言”,来说服读者,他所描述的情况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只“述而不作”,依靠古代所传下来的权威。1632年,高一志出版了包括700条比喻的《譬学》。但是,写这本书之后,高一志很可能了解到,这样的文学材料缺乏历史的权威性。为此,他便写了《达道纪言》当作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具有修辞学色彩的材料。
高一志很可能早有写这本书的计划。 而且,我认为,在他在写三篇伦理著作时,他手里应拥有了很多翻译好的“纪言”。他可能会用这些稿子做教材,以供中国人作文和发言时利用这些“纪言”。但是,为了让这种修辞学材料有更广泛的影响,他便与韩云合作整理这些“纪言”。如此,当一个学生要写一篇论文或发言时,他便可以自由地从中找到他需要的材料,使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更具说服力,收到文雅的效果。
在高一志的教育理想里面,经典是一种基础,他写道:“故书乃幼学所最急学,而舍典籍犹舍毛羽而欲高飞,岂可得乎?” 而且,高一志主要试图从经典中选择一些“纪言”,使这种成文的文化变成一种口语上材料,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在《譬学》里面,他更详细地解释修辞学的功能:“故圣贤经典,无不取譬。虽夫妇之愚,皆可令明所不明也。且此譬法,非特使理之暗者明,又使辞之直者文,弱者力,凡欲称扬美功,贬刺恶德,启愚训善,策怠约狂者,可以撰悦其耳,深入其心。” 这里,他强调一个“比喻”的功能:本来不明白的道理,使人们能通过“比喻”明白,而深入自己的心。
文艺复兴时期,斯多葛学派(Stoic School)获得了新的生命,人们发现这个学派具有高度的伦理性质。教会没有排斥这个学派,而接纳它的很多方面。比如,在耶稣会里,塞涅卡被普遍接受,甚至于被称为“我们的塞涅卡”(noster Seneca)。
耶稣会来华之后,他们很快把儒家和斯多葛主义连接起来。这两个学派都以道德修养为核心。他们都把个人生活(内圣)和公共生活(外王)密切地连接起来。它们的伦理思想主要不居于形而上的哲学系统,而基于智慧的历史典范,即“圣人”。
1593年,利玛窦给耶稣会总会长阿奎维瓦(Acquaviva)写了一封信,他把孔子和塞涅卡作了比较。 1597年,在另外给阿奎维瓦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强调它们之间的文学特征,把儒家经典与西塞罗的书信作了比较:“在同一时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繁荣的时候,在他们当中也有学术繁荣,他们写成的伦理著作,不用科学方式,而用“纪言”的方式。某些主要人物写了四书,这些书被人们昼夜阅读。它们在篇幅上不超过西塞罗书信,可是随后的评论和注解,还有评论的评论,还有其他关于它们的论文和话语至今汗牛充栋。” 应该注意的是,利玛窦认为,斯多葛主义接近儒家,有两种原因:第一,伦理思想的内容;第二,文学特色。在这第二点上,利玛窦认识到,中国人并不欣赏亚里士多德所写的长篇大论,而更欣赏西塞罗或其他斯多葛学派的简短“纪言”。毫无疑问,高一志试图在 《达道纪言》上接近斯多葛学派和儒家的榜样,而希望这种西文经典能变成中国经典。因此,《达道纪言》中的大部分“纪言”属于斯多葛学派:布鲁塔克(48条自己发表的纪言,还加上40条他自己记录别人的纪言)、塞涅卡(30条)、西塞罗(7条)。
五、《达道纪言》与话语团体
当然,标题中的“纪言”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即“纪纲的言论”。按照这个理解,标题强调伦理特点,而很清楚,标题的前两个字“达道”也代表这个意思。在《中庸》里面,“达道”与“五伦”有很密切的关系:“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第20章)。因此,我们能觉得,《达道纪言》不仅是一本具有修辞学性质的书,而且更是一本伦理学的书。修辞学作为劝告他人的技艺,可是这个技术本身不是中立的。学生在学习修辞学时,也同时在学习伦理。
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Couplet)在谈及《达道纪言》时说:“关于伦理哲学,包括市民和家庭,应用比喻和记言来说出。” 这本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说服力以及他们的伦理观念。为此,伦理学必与修辞学结合,通过修辞的方法来推广伦理观念。
传教士还试图建立团体,这些团体可有几种模式:除了皈依天主教而参与圣事生活的信徒外,还有对天主教有好感的学士。对这第二种非宗教性的团体模式而言,建立文集和经典就显得很必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达道纪言》堪当团体伦理关系的新榜样。其实,晚明的很多知识分子想避免王阳明弟子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寻找一种新的团体模式。比如,韩云的弟弟,韓霖 (1600-1649年),试图形成一个恢复“乡约”的团体模式。他在《铎书》(约1640年)中把儒家原则和基督宗教原则综合起来。按照韩霖的看法,传儒家的道或者传基督宗教的道理都一样,只能在“人伦”里面发挥,因为这些“人伦”基于天性。 那时,每月朔望的第二天,韩云、韩林和绛洲的士大夫都聚会。他们在明朝即将崩溃的危险形势之下,宣讲《圣谕》,还轮流发言。 我们可以理解,在这样的会场上,《达道纪言》这本书很可能被用作发言的引据。虽然韩氏兄弟受了洗,可是大部分没有皈依天主教的人,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宗教的性质。
晚明,很多人非常关心他们的伦理生活,于是很多“善书”应运而生,以作培训和支配个人和团体的伦理生活之用:四书五经和它们的通常解释;日用类书,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1560年) 或《幼学易知杂字大全》(晚明);罪过表格(如用来反思自己的罪事和善事的“功过格” );自我诉讼的书,如刘宗周 (1578-1645年)在他的《人谱》里面所描述的“讼过法”。 即使这些方法都强调个人的伦理责任,它们都被用作一种团体的伦理话语。在这一伦理话语中,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提供了具有权威性的示范。同样,《达道纪言》,通过西方古典,企图形成一种新的伦理话语力量,来支持新团体的生活。
因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达道纪言》之于团体生活的意义,它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团体的基础。我们也同样可以了解为什么在五伦中,朋友关系占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绛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就是理学儒家辛全(1588-1636年)。辛全的很多弟子都偏向西学,帮助耶稣会士出版著作。 那时,在西方传教士与当地知识分子和官吏兴起很浓厚的合作精神。下面这个“纪言”便是这样的一种政治的暗示:
11都略曰:“羞心乃友之固城也,一念去羞,则有求非义者,即有将顺之者,彼此无所忌矣。”
If you dont see the virtue of friendship and harmony, you may learn it by observing the effects of quarrels and feuds. Was any family ever so well established, any city so firmly settled, as to be beyond the reach of utter destruction from animosities and factions? This may teach you the immense advantage of friendship. [M. Tullius Cicero, Laelius, De Amicitia, N. 23]
在西方思想里面,把个人灵魂看作一个城市有渊源的传统。 而且,在古希腊拉丁思想里,友谊是政治的基础。在上面的“纪言”里(本来属于一封信),西塞罗强调,友谊是在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里,朋友关系一直被怀疑是否摆脱正当的政治框架,即君臣关系,而试图组成反政府的党派。如此,儒家认为,由于友谊没有君臣或父子关系那么基本和稳定,所以不可能提供一种政治基础。这个“纪言”或许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团体所面对的形势:拥护了明朝和救国图存,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自己成立一种新的团体,吸收西学,但却被人怀疑要组成一个党派来推翻政府。
结论:当今国际关系与修辞学
这篇论文没有分析这些“纪言”从西文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也没有分析它们所反映的晚明伦理问题。这个研究只想表明《达道纪言》的修辞特色,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观察伦理学的运作。进一步的研究当然应该注意到,这种写法与中国文化内部的修辞传统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最后,我想指出,双方文化的交流需要一种话语上的共同基础。为了个人与自己的对话,为了个人与他人的对话,认识和理解经典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经典能够提供一种共同语言的空间,通过诠释它们来展开无限的创意。另外,诠释原则需要利用共同理性。
由于对经典的忽略或封闭性的诠释,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在今天重新抬头。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只了解本土文化、民族、宗教的经典是不够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世界公民都需对世界上的四大传统,即中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的经典有相当深入的理解。
有人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能够跨越不同语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希腊和拉丁的经典在第十六世纪被成功地译成了各种欧洲语言。在同一时期,一批西方人和中国人参与了双方经典的翻译、理解、比较。我们今天应继承前辈的努力,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更有理由去加深对各种文化的经典作深刻的理解。这些经典不应是一堆死文字,而应在我们的话语中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