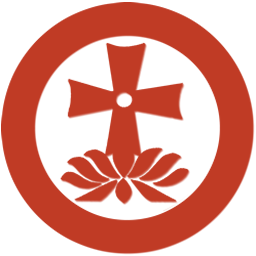康熙初期的广州事件(1666—1671)① 过后,对于清代中国天主教葬礼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系统丧葬礼仪的创制。在1685年广东起草的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里,中国和天主教的礼仪传统交织在了同一种礼仪程序之中。② 这份独特的文献还显示了葬礼的两项主要功能:第一,通过家庭,将死者转变为祖先;通过天主教团体,将死者转变为诸圣团体中的一员。第二,增强家族群体和天主教团体的凝聚与团结。中国天主教葬礼,被纳入了以中国葬礼为基础的框架中;天主教礼仪中的关键性元素,被嫁接到了中国原有的框架上。
一、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
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规定了从死者亡故到遗体安葬,参与者所要进行的不同活动。这份指南有四种不同抄本:A.临丧出殡仪式(早期抄本)③;B.临丧出殡仪式(晚期抄本)④;C.丧葬仪式(早期抄本)⑤;D.丧葬仪式(晚期抄本)⑥。这四种抄本分别称作文本A、文本B、文本C和文本D,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并且有可能按照年月先后顺序(A最早,D最晚)写成。⑦
文本A没有署名,但文本B、C、D封面上的注释,透露了有关这些文本历史的一些信息。⑧ 文本B有一条耶稣会士方济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 1632-1692)用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写的短注:“我命李安当相公(Antonio Ly)于1685年1月编成本书。”⑨ 这则注释很重要,因为一开始它就承认,中国合作者李安当是文书的主要作者,方济各只是下令编纂文书的人。文本C的注释也有方济各的署名,日期是1685年5月16日,其中透露了此后文本改编的一些信息:“本文源自我让李安当相公编写的另一文本。它由罗文藻(Basilitano)主教阁下的李良相公(Leontio Ly)修订,他希望能将其批准并签署实施。尊敬的利安定(Agostinho de S. Pascual)修士对它有所保留,因为他希望在第十一章必须增加一份使礼仪纯粹的声明。”⑩ Basilitano主教即罗文藻(Gregorio López, 1617-1691),他是多明我会修士,1654年在马尼拉被任命为神父,1685年4月8日在广州晋升为主教。利安定(Agustín de San Pascual,约1637—1697)是圣芳济小兄弟会(OFM)的成员,1671年来华。他最初服务于福建多明我会教团,1677年至1683年到山东重开圣芳济会教团。1683年底,他在广州积极活动,担任过罗文藻晋升主教时的助理神父。他用中文撰写了数篇论文,为在华西班牙圣芳济会修士拟定了几篇神父守则。1685年底,他被推选为任期五年的圣芳济会省长。(11)
抄本D的附注显示,本书的出版工作半途而止,这从方济各撤消签名一事可以看出:
由罗文藻主教阁下的李良相公修订的这份文书,第十一章附有关于净化向死者献祭的声明,未经我知晓,即由Bishop主教阁下和尊敬的余天明修士(Jo. Francisco de Leonessa)(12)、利安定修士两位神父签署。我否认与此事有关,并经各位同意,将我的名字从文书的首页删除;为使前面的签名失效,文书尾页我的签名、连同主教阁下的印章以及上述神父的签名,也一并删除。(13)由此看来,这份仪式指南并未出版。(14)
从上述历史及文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份指南原被设计成一种地方规定性文献,面向基层天主教团体,包括社会的较低阶层。同样清楚的是,这份文献并未与实践脱离。它不仅由两位地方教师编纂和修订,而且这份文献未被出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利安定的修改可能会改变当前中国天主教徒的实践。(15) 它与欧洲《罗马礼书》的情况不同,《罗马礼书》是神学家之间长期讨论的结果,神学家们不仅要考虑实践,而且要考虑到书面文献的悠久传统。这只是一份指南,它在实践地点附近起草,试图为已有的实践活动安排秩序。虽然有这些限制,这份指南仍是一份能向我们透露17世纪末某些葬礼活动信息的描述性文献。篇幅最长的文书B里面的规章,抄录如下:(16)
《临丧出殡仪式》李安当、方济各
[序]
一
圣教之礼,与本地无邪之礼,意不相同,所以不容侵杂。先该行圣教之礼,再用得本地无邪之礼。
[初终]
二
教中人若弃世,其家人即宜先报神父,请神父做弥撒,为先亡之灵魂。不该迟报,免灵魂之害。
三
通会长传知众友,齐集伊家念经。
[小殓(17)]
四
集众友,先迎尸入中堂。用床板,下垫白布一幅,放尸在上。尸前桌子,摆列香烛。
五
安座圣像、桌子、桌帏,排列香花蜡烛等物,务要清洁。
六
众友齐集跪下,圣像面前作十字,念初行工夫、天主经、圣母祷文、终后祷文各一遍。又念圣母六十三一串,念已完工夫,作十字。毕,兴。
七
众友到尸前,四拜,四兴,然后俯伏。尽举哀之礼,宜有节。
[大殓]
八
备办棺木,厚薄称家之有无。
九
备棺后,然后请会长及众友齐集念经。又将殓时向圣像齐揖跪下,作十字,念初行工夫,圣人列品祷文、殓前经。念已完工夫,作十字。毕,会长独自起身,用圣水洒尸,合念洒圣水经。毕,齐兴
十
收拾妥当,迎尸入棺,封钉。众友向圣像前跪下,作十字,念初行工夫、殓后经。毕,兴。
十一
安置棺木家堂中。棺木面前,设香案,品物多寡摆列。孝子跪下、上香、奠酒。事毕,众友揖退。孝子率家中人同举哀。毕,孝子跪前,叩谢众友。
[牌位]
十二
写牌位,上不必用“神”、“灵”等字,竟写“显考某公之位”或“显妣某氏之位”。
十三
亡者牌位前,不宜念经,但行本地之礼,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教友若要念经为亡者灵魂,当念于圣像前。
[吊]
十四
若有外教亲友来吊,送香烛可受。倘有元宝纸钱来,情上难即退还,可立时将水湿坏,不令他烧,决不许留在家中。外教亲友,作揖叩头举哀礼毕,孝子跪前,叩头答谢。
十五
若教友往吊外教,能送香烛、作揖、叩头、举哀。不得行外教一切邪礼,亦不得行教中圣功。
十六
教中人既十分苦心劝父母进教,父母偏执,至死不肯开心归正,此属本人自坏灵魂,孝子无可奈何。既行不得邪教之礼,又不得用圣教之礼,止能行古无邪之礼而已。
[做七]
十七
七旬之礼,除侵杂邪事,可用。
十八
若做七的时候,偶遇着瞻礼之日期,先要到堂听弥撒。完,随后能往伊家,做七旬之礼。
[成服]
十九
依本地之礼,七个七旬之内,惟首七、三七、末七习俗所通行的。因首七,是孝子孝眷定成服之日,并止吊;三七,是远近众亲友俱来设奠之日;末七,是丧礼完成,兼随后孝子出街谢客。
二十
若教中人要行此礼文,是日宜请会长及众友来其家,先做圣功于圣像前,后随孝子能供养上香于祖牌前,并率家中人同尽哭泣奠酒之礼。礼毕,亲戚及众友随后作揖、叩头、举哀,以尽若翁即吾翁之意。礼毕,孝子跪前,叩谢亲友。
[奠]
廿一
孝子所设酒馔,岂先亡能真享受乎?但已表孝心之文。能留亲友散馔,但孝子不宜饮酒,并能分送贫人,为祖先广惠,助其得天堂之福。
[诔,行述]
廿二
若外教亲戚有诔文来奠者,丧家宜预先送以死者行述,庶不令他侵入邪教之言。
[行述式]
廿三
首序,亡者某公、讳某、字某、圣名某、生于厶年厶月厶日、卒于厶年厶月厶日,幸邀主宠安终,享寿若干。次述亡者某公生平善德,自厶年奉圣教、昭事天主、恪守规诫、孝敬父母、慈恤幼孤,或其生前甘受苦伌、诸般之美行,真实称述可也。又次则述其现在孝子孝孙,皆奉圣教,克继父祖善志等語。末启亲友云:倘蒙俯赐诔诵显扬。幸教我伯或叔子孙,所当为之正向,以法祖之善德。无任哀感之至。司书侄某拭泪谨述。
[治葬]
廿四
出殡日期,听孝子自订,但不要碍瞻礼到堂听弥撒之日期。
廿五
出殡前几日,宜预请会长诸友。
廿六
若有人请教友守夜,是夜定念经三次:起更一次,半夜一次,将明一次。
[发引]
廿七
送殡之日,教友至亡者家里圣像前,念经如前头规矩。念毕,就摆列送殡的物件。先用吹手,次列旗旛,次十字亭,次天主圣像亭,又次总领天神亭,又次圣名亭。用得提炉宫灯,左右教友戴孝,拈香持蜡。末后棺柩,其柩上装紬彩。老少诸友序次而行。孝子扶柩鞠躬,孝眷人等,俱随棺后。
[及墓,下棺,反哭]
廿八
棺木到山停止。众友向十字亭齐揖跪下,作十字、念初行工夫、圣母祷文、安葬前经,各一遍。已完工夫毕,会长起身,将圣水洒琢洒棺,念洒圣水经。下葬掩土。毕,众友向十字亭作十字、初行工夫、圣人祷文、安葬后经。已完工夫。毕,兴。孝子跪前,叩谢众友。
廿九
葬礼完,即迎十字等亭,照前摆列回家。会长及众友同到其家,圣像前跪下,拜谢天主。毕,兴。然后安先亡牌位于香桌上,摆列品物。孝子跪下、进香、奠酒,并率家中人拜。毕,孝子拜谢众友。
三十
若孝子要款待回来的众友,随便相留款待,亦能送点心。
[清明]
卅一
每年清明日,教友能到山上拜坟。若此坟是葬奉教的,先念经,求天主为亡者灵魂。然后点蜡上香供养。若是葬外教的,不得念经,但点蜡上香供养而止。
卅二
拜坟压纸不妨,但用不得纸钱。能用素白纸,将土压之坟上,意令人知此坟有人看顾。
二、清初天主教礼仪与地方风俗
虽然《临丧出殡仪式》是明确面向天主教徒的,但从一开始,它就不准备仅仅描述天主教的丧葬礼仪。虽然它告诫不要将天主教与(非迷信的)当地的礼仪不恰当地混杂在一起,但通篇文献都展示了怎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文中的“本地之礼”主要是指“粤中(广东)之礼”,(18) 这些风俗明显是不同传统的混合物。
《临丧出殡仪式》所推荐的葬礼基本结构,与明清时期中国通行的葬礼结构相吻合。它大体上依据《礼记》中勾勒出的、后来由朱熹等人在《家礼》中加以简化的那种经典模式。(19) 文本A中(第二则),有几处直接提到了中国葬礼仪式的某些主要环节,诸如《家礼》中提到过的小殓和大殓。(20) 和晚明时代一样,那些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天主教徒的中国人,对这种经典的葬礼程序可能极为熟悉。这一点可以从同时代中国天主教作家的其他著作中推断出来。例如严谟(教名保禄)与其父严赞化合写的《李师条问》(约1694年成书),就是一部非常系统的著作,在书中他们依据经典,对李神父(有可能是耶稣会士李西满[Simao Rodrigues, 1645-1704])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在回答“丧礼各等葬礼如何”时,作者大量引用了《家礼》中有关葬礼的章节。(21)
在17世纪,宋明儒学家的礼仪制度落实得既不全面,也不具有排他性。经典仪式和源于佛教、道教的礼仪,在许多地区实际上互为补充。例如,“做七”和七七的礼仪——从亡故之时起,每隔七日,家中要请和尚或者道士来念经,直到第七个七天(第四十九天)。虽然主要源于佛教,但七七之期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吊唁以及崇奉亡故的父母的特定日子。因此“做七”,指的是在每个第七天举行的一大套活动,甚至可以没有僧人的参加。“做七”的具体礼数繁琐,并且因地而异。从上面这些资料可知,按照广东本地的风俗,只有头七、三七和七七才举行仪式
(B19)。(22) 文本B、C和D(B17)允许用七七之礼来补充天主教葬礼仪式,只要其中不掺杂迷信的语言(文本C、D)和活动(文本B)。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七七的仪式应该不会邀请佛道僧侣。17世纪晚期的中国天主教葬礼,明显建立在《家礼》的基础之上,并且排斥了大多数外在的佛教、道教活动。
从一开始,这四种抄本的仪式指南就混合了不同传统。它的基本架构,是传统的中国葬礼模式。在这种架构之内,天主教、新儒家甚至源自佛教的某些礼仪,融合在了一起。对于这种礼仪的变化(以后它还将深入发展),有一个事实是需要着重强调的:这项指南,是建立在构成中国礼仪“基本结构”的一组活动、程序和表演的基础之上的。在晚期帝国时代,这种基本结构之内的活动,在整个中国差别都很小,不管阶层、身份或者物质条件如何。(23) 这项以大殓、送葬和安葬为中心的指南,证实了这种基本结构的存在,虽然它与天主教礼仪交织在了一起。
三、葬礼的参与者及其活动
虽然仪式指南的各抄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有关葬礼的人类学研究,反映出了它们的共同特征。下面首先从三个主要问题(参与者是谁、他们表演哪些活动、在何处表演)入手,分析这些共同特征;其次根据研究的结果,分析中国天主教丧葬仪式的含义和功能,观察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构建具备有效礼仪的团体(表5.1)。
神父
在欧洲指定性文献里,最显眼是地方神父。在17世纪的欧洲葬礼中,他们显然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但在这份中国人改编的地方礼仪指南中,神父被弱化为一个边缘的角色。指南明确提到神父的地方,只有一处。在仪式的最初,死者一去世,“其家人即宜先报神父(A1作“铎德”),请神父做弥撒,为先亡之灵魂”。在两次提到弥撒(不能因举行地方丧礼仪式而不参加弥撒)之时,神父的角色仍不明朗:“若做七的时候,偶遇着瞻礼之日期,先要到堂听弥撒。完,随后能往伊家做七旬之礼”;下葬的日期“听孝子自订,但不要碍瞻礼到堂听弥撒之日期”。神父的边缘化,从举行礼仪活动的地点中进一步显现出来:根据欧洲指定性文献,尸体要从死者家中运往举行葬礼弥撒的教堂,然后从教堂运往墓地;而中国的仪式指南,却只把举行仪式的地点定在亡者家中和墓地。神父并不介入这些仪式。他为死者举行的弥撒在教堂中进行,而且不要求死者家属参加。
《临丧出殡仪式》证实了神父角色的边缘化,这在汉译欧洲指定性文献(尤其是伏若望的《善终助功规例》和利类思的《善终瘗茔礼典》)、天主教徒团体的会规和广州会议的决议(尤其是第34条)中都可以看到。天主教神父人数的减少,可以解释他们被边缘化的原因;而在传统中国葬礼仪式中,司仪(现代西方文本中,他们通常也被称为“祭司”)的低微角色,或许也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司仪所占据的地位模糊不清,按华琛的说法,是一种“制度化的边缘”(institutionalised marginality),因为他们长期暴露在死亡的玷污(也即根据广东人的观念,被尸体散发出的空气所污染)之中。因此在葬礼期间,他们尽力避免将自己太多地暴露在这种污染当中。而且,虽然所有男性参与者通常都参加送葬,但司仪却从不将棺柩陪护到墓地。(24)
中国天主教仪式中也有内容显示,天主教团体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葬礼中含有明显的危险。中国有关玷污和混乱的潜在危险的传统观念,是这种威胁感的来源之一;指南中建议供桌要清洁(B5),哭泣要有节制(B7),并使用圣水(B9)。另一个来源,是天主教关于迷信和偶像崇拜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教外亲友的举动中所包含的(B14、B16)。天主教神父和中国司仪之间的比较不能引申得太远,因为中国传统的“司仪”的概念与天主教的概念差别很大——中国多数的礼仪专家都可以结婚,并且通过为他们所在的团体服务来养活家庭。(25) 而且,在天主教传统中,死亡并非真被认为是不洁的。尽管如此,许多礼仪文书——像前面提到的天主教团体的会规,依然在葬礼仪式中只为天主教神父提供一个边缘角色。这种边缘性与中国葬礼中司仪的角色相吻合,但这项角色类似于10世纪之前欧洲的葬礼传统。
天主教团体
在这些文本当中,天主教神父的边缘角色与天主教团体的主导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葬礼中多数的核心角色,似乎都被天主教团体的成员所占据,这些成员通常被称作“众友”(B6)、“教中众友”(C6)或者“教友”(C7)。天主教团体成员,是下列关键仪式中的主祭:小殓(B4—7)、大殓(B9—11)、改造过的七七仪式(B20,A15)、葬前守夜(B26)、安葬之日的各种不同仪式(B27—30)以及清明节的礼仪(B31)。这些活动都发生在死者家中或者墓地。这种团体(它总是作为一个群体而被提起,唯一被单独提及的个人,是会长)以及团体的活动,是中国天主教葬礼与中国儒家传统差别最为明显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与教派传统的相似之处。
团体成员的活动对于决定他们的角色非常重要。除哭泣和作揖,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念诵祷文。按照中国传统,念诵一般由司仪或者专门为此而请来的一群僧人进行。(26) 和在会规中一样,在《临丧出殡仪式》里这项任务由一群世俗天主教徒来集体承担。天主教葬礼在这个方面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教派葬礼,教派组织的世俗成员在其中负责诵经。(27) 不同抄本的指南中都规定了相当一部分必须要念诵的祷文。文本B中共有四条详细的祈祷指导:首先在小殓之时(B6),其次是大殓(B9、B10),最后在安葬之时(B28);文本A中还有另外三则看护时的祈祷指导(A8、A9、A10)。(28) 这些集体祈祷遵循日课(许多信徒在日常祈祷中人手一册)规定的一般的集体祈祷次序:跪拜,作十字,初行工夫,各种祈祷,已完工夫。多数的祷文都为人熟知,不是专门面向葬礼的:《天主经》、《圣母经》、《申尔福》、《信经》、《圣母祷文》、《圣人列品祷文》,以及反复念诵的祷文(《天主经》重复三十三遍、《圣母经》六十三遍)和《玫瑰十五端》。(29) 这说明天主教团体之所以能够积极参与念诵祷文,是因为大多数信徒都对这些祷文非常熟悉。仪式指南还提到了专门用于这种特殊礼仪活动的祷文:《终后祷文》、《殓前经》、《殓后经》、《安葬前经》和《安葬后经》。这些祷文也可以在伏若望、利类思编订的那些汉译欧洲礼仪手册中找到。(30) 但这些仪式中祷文的题目,和指定性礼仪手册中的题目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很难断定这两本书(或者另有一部什么书)是否真的曾被用作参考。(31) 这些手册中的祷文是否为人熟知,这点也不清楚。
关于天主教团体举行礼仪活动的特定场所,他们总是跪在“圣像”(可以是一个十字架,或者是天主甚至圣母的画像)前诵经。除了下跪,天主教团体还采纳了传统的表达敬意和哀伤的方式:四拜、俯伏、作揖、叩头和举哀。(32)
这些祈祷人群的参与,是判定死者是否天主教团体成员的一项重要标准。(33) 而且,它们还是传播天主教理念和习俗的重要平台,因为在这些场合中,天主教团体有机会深入到家族圈子的内部。(34) 最后,这些礼仪活动为参与者增强他们的内部联系,提供了机会。
会长
中国天主教团体内部的核心角色是会长,这在广州流放之前的天主教团体中已是如此。指南中明确提到,由会长向团体成员通知某人的死讯(A1b,B3)以及下葬的日期(A6b,B25)。除了参加团体的祈祷(B9,B20,A12b=B29,A15),会长还在入殓和安葬的仪式中担当中心角色。在前一个仪式里,他独自站起来向尸体播洒圣水(B9),念诵《洒圣水经》(即Asperges me(34)),并且在第二个仪式中向遗体播洒圣水(A12=B28)。然而指南中没有提到上香。
会长的中心角色,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天主教团体自身在葬礼仪式中所占的中心地位。
孝子
天主教团体及其会长,某种程度上遮盖了作为事主的孝子的角色。“孝子”这个词,指南在有关入殓之后的描述中第一次提到。现在还不清楚“孝子”是指所有守孝的儿子,还是所有的后代,或者这个词仅指丧主者——按中国传统,一般是在世的年纪最长的儿子或指定的男性继承人。(36) 在传统中国葬礼中,他负责确保礼仪举行得合乎社会的要求。而在广东人的葬礼中,丧主只做主持仪式的礼仪专家命令去做的那些仪节。(37)
孝子的角色证明,中国天主教葬礼的主要礼仪活动场所,的确是在死者家中。根据中国天主教仪式指南,孝子在死者家中举行的下列仪式中担当角色:大殓后的仪式(B11),吊唁(B14)和七七的仪式(B19;B20;A15)。家庭成为中国天主教徒举行丧礼活动的主要场所,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天主教和传统中国葬礼之间的差别。按照欧洲礼仪,葬礼在死后很短时间内(一到三天)举行,因此尸体很快就从家中运走。与此相反,按照中国传统,安葬之前棺柩可以在死者家中的堂上停放数月。《临丧出殡仪式》中的中国天主教葬礼规则,符合中国主流的思想观念。按这种观念,中国人一生经历的主要礼仪(冠礼、婚礼、丧礼)都被认为是“家”礼。这样一来,仪式指南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早期的传统类似,那时葬礼的主要场所也是在家中,而不是教堂。
天主教团体的成员都在“圣像”前举行活动,而孝子是唯一在祭桌或祖先牌位前面行礼的人(B13,B20,B29)。《临丧出殡仪式》规定,圣像和祭桌要摆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像晚明福建某些地区的做法那样,将一个放在另一个的后面。这种地点分离,显示了礼仪活动的不同角色和范畴。孝子和其他守孝的亲属一样,要在首七穿着丧服(B19),以此来表达他们与死者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在家庭结构中已经改变的位置。而天主教团体的成员,只在送葬仪式中穿着丧服(B27)。
孝子的活动,都属于中国葬礼(和其他)仪式中未被传教士认定为“邪”的活动:
上香、供养和奠酒(B11,B20,A12,B29)。孝子是指南中唯一提到的行这些礼仪的人;唯一的例外,是在清明节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在天主教徒的坟上点蜡、烧香和上供(B31)。孝子还带领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宾客、教友,作揖、叩头和哀号。而且孝子还负责接待客人,在下葬之后款待宾客(B30),拜送客人以及向亲戚朋友叩头致谢——指南中有数条与这类活动有关的内容(B11,B14,B20,B28)。最后,由儿子们决定安葬的日期(B24),并且在送葬时站在棺柩旁边的一个特殊位置上(B27)。
孝子的礼仪活动显示,他们所进行的,是《家礼》等中国传统礼仪手册规定的基本活动。
亲友
葬礼仪式中的参与者,还包括与死者相识的一大群人。大家族的成员们(“家中人”和其他亲戚)参加各种葬礼仪式,并用传统的作揖、叩头和哀泣等方式致敬致哀(B11,B20)。三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一天远近的亲友,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非教徒,都来参加祭奠(B19)。亲戚和朋友们也通过作揖、叩头和哀哭等传统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悲伤和敬意(B14)。虽然这些外来参与者可能人数众多,但对他们的角色却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定。
这些亲戚朋友之中,可能有许多教外者来行“外教之礼”;到异教徒家中吊唁的天主教徒,也可能会目睹这种礼仪。在这种互动之中,天主教礼仪和那些被认作迷信的礼仪可能会产生冲突。
四、礼仪活动实现的转化
对参与者及其活动的总体考察显示,葬礼仪式参与者主要有三个圈子,他们对应于三组具有典型特征的活动。第一个圈子由天主教团体成员及会长(包括处在边缘地位的神父)组成。这个圈子的活动是口头的,与书面文献(在圣像前面念诵或者大声朗读的祷文)相关。第二个圈子由孝子组成,其活动特征由仪式表现出来:供献食物、酒和其他物品,并在祭桌或者祖先牌位前上香。第三个圈子是范围更广的亲友团体。他们的活动(其他两个群体也如此)是一些身体的情感表达:俯伏、作揖、叩头以及哀哭。
指南第二十条(B20,指导教徒举行七七的仪式)显示了这些不同的群体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若教中人要行此礼文,是日宜请会长及众友来其家,先做圣功于圣像前,后随孝子能供养上香于祖牌前,并率家中人同尽哭泣奠酒之礼。礼毕,亲戚及众友随后作揖、叩头、举哀,以尽若翁即吾翁之意。礼毕,孝子跪前,叩谢亲友。
《临丧出殡仪式》对天主教徒举行七七之礼和其他许多礼仪的方式,都有详细的描述;但是,这些不同礼仪有何含义,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中的活动如何将这些含义表现出来?总的来说,仪式与变化有关,尤其是像葬礼这样的生命转换之礼。(38) 特别是丧葬礼仪,与生命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相关。但仪式变化的含义,通常并不被表达出来。这在礼仪文本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它们明白地指出要做什么,却不说明这些仪式的意义。它们关心的是行为正统(正确的实践)而非观念正统(正确的信念)。(39) 虽然分析这些文本的深层含义需要谨慎,但还是可以弄清它们所暗示的是哪种变化。这里遵循的步骤,是将参与者、他们的活动以及活动场所放入一套连贯的情境之中,以重现它们的含义。
最为明显的转变,是由死人变为祖先。这种转变是将生物学上的死亡变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延续,家庭是发生这种转变的主要场所。在这一过程中,食物供奉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转变通过孝子的角色和活动表现出来。在临丧出殡仪式中,孝子是唯一献食奠酒的人。这些活动在祭桌或祖宗牌位前面进行,这是孝子特有的活动地界;例如,天主教团体就不许在祭桌前念诵祷文。祖先牌位前面允许举行本地仪式,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B13)。这句引文对《中庸》原文(第三章曾经提到)稍有改动,增加了两个“事”字。如此一来,这句话就在事死和事生之间建起了一个简单的比较。这就和早期传教士对“如”的解释(用来强调人们相信灵魂并不在牌位上)联系了起来。
从死者到祖先的转变,只为发生的礼仪活动提供了部分的解释。考虑到天主教团体的重要性,这种由肉体的死亡到社会意义的延续的转化,不只发生在家庭之中。受《宗徒信经》中“诸圣相通功”(40) 这一经典观念的影响,天主教团体也被看作是这种社会延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中国天主教葬礼受到了欧洲主流天主教死亡观的影响——那时的死亡观是悲观的,需要为“亡者灵魂”念诵代祷经文或者举行弥撒(B2,B13)。(41) 除了这种个人救赎的需要之外,还有一种天主教观念认为,死者最终会融入诸圣的大家庭,得以赎罪,并且获救(universa fraternitas)。(42) 而且,人们相信守丧者可以向诸圣团体恳请,请求他们代死者祈祷。生者和死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欧洲概念的汉语翻译,是建立在“功”这个核心概念基础上的。为亡者背诵天主教祷文被称为“作圣功”(B15,B20),“圣徒群体”被翻译成“圣神(诸圣)相通功”,告知教徒的死讯并邀请团体成员为亡者祈祷的传单,后来被叫作“通功单”。(43)
在《临丧出殡仪式》里,这种关于死后生活的普遍观念,是通过天主教团体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例如,代替祈祷的祷文就在生者、死者和诸圣(因为不管在祷文的内容还是措辞上,诸圣团体都受到了恳求)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些祷文包括《圣母祷文》和《圣人列品祷文》(B6,B9)。而且,诵经总是在圣像(天主、圣母或者圣人的画像)前面进行,刚才已经提到,不是在祖先牌位面前。在葬礼游行中,当遗体和天主以及圣弥尔额的画像一起被抬着前进时,诸圣团体也受到了恳请。当时的传教士肯定不会声称死者会立即进入天堂的诸圣团体。不过,这些参与者、他们的活动以及活动的地点表明,一个由生者和死者组成的天主教团体与祖先群体(ancestral community)形成了互补,死者在其中可以受到诸圣的帮助和支持。
天主教团体的互助——慈善活动和代替祈祷,同样可以将死者引入诸圣团体。这在《圣教规程》有关帮助贫困家庭的死者的规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十五 教中有贫者死,教友宜为其通功、念经、做追思。若有无力殡葬者,亦当留心助其殓。具此系十四哀矜葬死者之功,宜行相通之谊。(44)
因此天主教的“做功德”(不仅用祈祷,还有经济互助的形式)建立起了生者和死者的天然联系。
中国天主教葬礼中有两种转变:死者通过家庭转变为祖先;通过天主教团体转变为诸圣团体中的一员。而且,通过积极参与葬礼,进入家族圈子,现实中的天主教团体将家族组织扩展为一个更广大的群体。参与天主教仪式,将人们和一个更为广大的天主教群体(在更早的时代和其他地方,他们也参与类似的仪式)联系了起来。(45)
五、葬礼仪式的功能
礼仪的功能不仅是作为转化死者的媒介,而且还是增强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工具。(46) 杨庆堃在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传统丧葬仪式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重申家族群体的凝聚与团结。(47)在中国天主教仪式指南中,家庭内部的角色——孝子——被清楚地加以肯定。“孝子”是表演特定礼仪活动的一个特殊群体。当孝子履行他们的特定礼仪角色时,仪式就具备了一种凝聚家族近亲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巨大力量。
这种对团结与凝聚的强调,是以某些特定的礼仪活动作为媒介的。一个例子是礼仪性的哭泣,这在许多文化中都很普遍。不管哭泣是否出于真心,它都是一种群体凝聚与团结的证明,是一种对失去了一位群体成员表示关心的方式。根据参与者社会地位或者角色的不同,这种礼仪性的哀哭重建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情感联系。那些不哭的人,会被家族成员当成不仅是对死者,而且是对这个群体不忠。(48) 欧洲描述中国丧葬仪式的文献,经常会明确提到作为这些仪式的一项重要特征的号哭,还指出偶尔的过度哀伤,(49) 有时还将士绅“虚伪的眼泪”与中国天主教徒“真诚的泪水”进行对比。(50)《临丧出殡仪式》也提到了哭泣。它被当作一种明确的礼仪,在A2和B7中被称作“举哀之礼”。(51) 例如,孝子要带领家中人号哭举哀(B11)。文本A规定哭泣应该“宜节不宜过伤”(A2)。天主教团体成员等外来吊唁者,也要这样举哀。在欧洲,哭泣也是葬礼的一部分;但指南中提到的举哀之“礼”,欧洲指定性中是没有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哀哭在中国被赋予的特殊重要意义。
杨庆堃进一步指出,家族群体得以巩固,不单是通过守丧者展示性的举动,还通过重申与亲族之外更广的社会圈子的关系,以及重新证明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巩固遇丧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一种努力。《临丧出殡仪式》显示,履行这种职能的礼仪活动,在向亲戚们发出讣文的那一刻就开始了(B22、B3):讣文不仅向他们通知丧事,还邀请他们参加送葬和丧宴。对亲友的招集,以及招来的亲友群体的规模,显示了这个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52) 这种社会功能还在三七那天组织的宴会,以及七七之日孝子出街谢客中表现出来(B19)。指南是一份关于仪式程序的文本,因此较少关注诸如赴宴、备办食物和社会交际之类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招待客人不是葬礼的一个重要方面。(53) 另一种重申家族地位的方式,是在送葬仪式中对家族财富和影响力的展示。
群体的凝聚力不仅影响到家族,而且涉及天主教团体。在传统中国葬礼中,庞大的专家(司仪、乐师、抬棺者、僧侣)和非专家团体,参与者人数众多。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在《临丧出殡仪式》中天主教团体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被提及的。一项主要的特殊任务——念诵某些特定的祷文,把天主教团体自身与死者家族,以及亲戚群体区分开来。在某些地点不允许表演某些仪式,通过这种做法,天主教团体也将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
六、结论
在前文中,耶稣会中国教团早期对葬礼仪式的描述,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中国天主教丧葬礼仪的发展,以某些欧洲和中国仪式的并行(juxtaposition)为特征,它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相互影响。然而1685年起草于广东的这本《临丧出殡仪式》显示,最晚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丧葬礼仪被从“中国的”和“天主教的”葬礼传统中创造出来,它们在同一个仪式过程中交织在了一起,虽然仪式的某些部分,在时间或者地点上可能分头进行。这个结果可以形象地比作植物的嫁接。新元素、扦枝(欧洲葬礼仪式),被嫁接到了一种事先存在的稳定环境或者树干(中国葬礼)上。在新的中国天主教葬礼中,中国葬礼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并成为新元素生长的基干。新嫁接过来的礼仪,与欧洲天主教本来的传统并不相同;在中国,它们经过改造,被纳入到以大殓、吊唁和安葬为主要环节的中国框架中来。在新创的中国天主教葬礼中,死亡和安葬的时间间隔不再像欧洲那样短暂,而是和当地传统一样较为漫长;尸体现在也被放进密闭的棺材里。葬礼仪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家庭成员和天主教团体,而不是神父。欧洲的墓地靠近教堂,与此不同,中国天主教徒的墓地是在城市或者村镇之外,而且遗体伴随着一场精心准备的送葬仪式运往墓地。但扦枝、新元素也给原来的基干带来了一些变化:天主教团体的仪式扩充了中国的家礼。中国天主教葬礼的两项主要功能,揭示了新的天主教元素对原有礼仪的影响:第一,死者通过家庭转变为祖先、通过天主教团体转变为诸圣团体中的一员;第二,加强了家族群体和天主教团体的凝聚与团结。这种嫁接的一项区别明显的新特征是:在团体的礼仪活动中,语言的主导地位超过了行动。同样是通过嫁接,传教士们认识到,某些天主教元素可以公开地展示。正如很难根据早期的外形来鉴别一株植物嫁接样本一样,这种新礼仪不能被排他性地称作“天主教的”或是“中国的”;它只能是“中国天主教的”。
另外,《临丧出殡仪式》还阐明了前面曾经涉及到的、这种相互交织的礼仪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结构性的变化——诸如围绕着大殓、吊唁和安葬等环节对天主教礼仪的调整,证实了中国葬礼基本结构的地位。因为即便是在与欧洲礼仪接触之后,这种基本结构仍被保留了下来。另一个方面是制度性的组织。指南展示了地方天主教团体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会长的特殊角色(这些角色也能从对负责葬礼的天主教徒组织的描述中找到)。在借鉴欧洲葬礼仪式时,似乎存在着一种选择:神父的角色被保留下来但边缘化了,而世俗角色却被提升并且放大了。最后,在早期时代已经被注意到并被全部接受的那些具体的礼仪表达形式,现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具体的礼仪被清楚地分配给不同的角色:有些只由孝子执行,有些分配给天主教团体成员执行,还有一些所有人都可以执行。
《临丧出殡仪式》清楚地揭示了团体的角色和团体中举行仪式的地点。试图通过葬礼来展示自己的天主教团体,似乎和中国宗教信仰具有某些共同本质特征,展现出与其他团体(尤其是那些具有佛教、道教传统的团体)的类似之处,这一点非常明显。这样的团体可以被称作“有效礼仪的团体”(community of effective rituals)。在这样一个团体中,人们被组织在一起并团结成一个群体,群体的生活节奏共同受到某些特定礼仪调节。这些礼仪活动通常依据礼仪历法(liturgical calendar)来安排,在天主教里依据的是天主教历法。传教士们将一种新的历法介绍到中国,这不只是提供了对时间进行中性划分的一些技术性方法。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他们还挑战了礼仪生活自身的基础:自然的时间转化为一种文化框架、一种不仅从文化上(culturally)而且从礼仪上(cultually)定义的时间。对礼拜天和其他天主教宗教节日(在此期间信徒们应该参加弥撒,并且预先斋戒准备)的引入,使得他们按照一种和具备有效礼仪的佛教或道教团体不同的时间节奏来生活。这些活动可能未被有效地介绍到所有地方,但在这种礼仪的层面上,各处流动的传教士们与和尚、道士或者当地的萨满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竞争,他们之间的差别经常被夸大。葬礼仪式不是按照日历举行的,它们发生得比较偶然,但即使在这种时候,天主教徒仍然必须尊重礼拜天和其他节日。
《临丧出殡仪式》和天主教组织的会规显示,葬礼的组织依赖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在葬礼以外的其他时候也定期聚会。这些仪式不仅构建了一个群体,而且群体的成员认为它们能够赋予意义并实现救赎,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仪式的举行是“有效的”(effective)。在和各种恐惧(对死亡和灾祸、魔鬼以及自然灾难的恐惧)的全面对抗中,这些团体的成员相互支持;仪式的功效得到了证明,人们高兴地发现“它们有用”,这似乎是他们加入和维持这类团体的基本动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团体也展示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其他特征:它们很大程度上面向世俗,并由世俗信徒管理;虽然并未被明确地提到,妇女很有可能在念诵祷文等仪式中担当传播礼仪的主要角色。这些团体也有依靠神父主持仪式的观念——他们只在举行弥撒时需要神父。团体所信仰的教义,被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吟诵的祷文,清楚地传达出有关死后生活的信仰。团体成员都相信仪式的转化力量,因此在仪式中可以为死者代祷。所有这些特征都揭示了葬礼之时,天主教团体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中国的环境。中国民众的信仰和礼仪塑造了普通人的生活,天主教的活动也用同样的方式提供了一套令人敬畏的仪式,它们是日常生活中救赎的媒介。
注释:
① 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与在钦天监供职的传教士就历法等问题发生争论,事后传教士被全体放逐到广州,直至康熙十年(1671)赦还。
②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17世纪的礼仪指南;18世纪的礼仪指南,参看巴黎外方传教会Joachim de Martiliat 1744年编订的《云南—四川地区丧礼吊唁仪式指南》,载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s du Se-tchoan, Paris: Téqui, 1920,卷二,第7—11页。
③ 《临丧出殡仪式》(早期抄本),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汉部)II, 169. 4;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卷5,第439—446页。
④ 《临丧出殡仪式》(晚期抄本),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I. 153;《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47—465页。
⑤ 《丧葬仪式》(早期抄本),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I. 164;《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67—479页。
⑥ 《丧葬仪式》(晚期抄本),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I. 164a;《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81—491页。
⑦ 虽然文本A很有可能是文本B依据的底本,但两者之间有重要差别。文本A更短一些,总共19则条款,而文本B有32则。文本A中有二三则条款在B中散为两则,有一则在B中散为三则;因此A1相当于B2和B3,A5相当于B9、B10和B11,A6相当于B24和B25,A12相当于B28和B29。文本A中有两则在B中合为一则,即A17和A19合为B30。两个文本间能够对应的条款有限:文本A的十九则条款中有八则(8、9、10、13、14、15、16、18)在文本B及后面几个抄本中没有保留。文本A中较为独特的,主要是那些对祈祷的指导。文本B篇幅最长,与文本C、D非常接近,但其中有两则为他本所无:B23(行述式)和B25(邀请会长治丧)。除了用词上的一些细微差别,主要区别在于B11(详下)。除去第11则中的一句话,文本C和D完全一致。
⑧ 文本A没有注文。
⑨ 《临丧出殡仪式》(晚期抄本),《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48页;参见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第205页.
⑩ 《丧葬仪式》(早期抄本),《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70页;Chan(2002),第214页(此处稍有调整)。
(11) 他的传记见:Sinica Franciscana Ⅲ, A. van den Wyngaert编,Quaracchi,1936,第333—351页;Sinica Franciscana Ⅶ, G. Mensaert编,Rome,1965,第123—132页。遗憾的是,他的通信中并未提到有关修订仪式指南的争论。关于他的中文撰述,参见Henri Bernard, “Les adaptation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ls à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 fran? aise de Pékin, 1514—1688”,载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10(1945),第1—57,309—88页:461,502,503,520号。关于牧灵守则,参看“Normae pastorales pro seraphica missione statutae, Cantone exeunte a. 1683”, Sinica Franciscana Ⅶ,第187—195页。
(12) Giovanni Francisco Nicolai de Leonissa(1656-1737), Sinica Franciscana IV, A. van den Wyngaert编,Quaracchi, 1936,第463—477页;Sinica Franciscana VI, G. Mensaert编,Rome,1961,第3—18页。
(13) 《丧葬仪式》(晚期抄本),《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82页;Chan(2002),第215页。这份文件于1685年5月15日签署(比文本C早一天)。
(14) Dunyn-Szpot也称,他不确定它有没有出版,见下注。
(14) 方济各认为,没有理由批评一种已经被耶稣会士作为固定形式采纳数年,而且在信徒们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信仰错误之污名的实践活动。本部分内容参见方济各1686年2月23日广州通信:“Controversia inter Basilicanum and Philippucium ob ritum quondam Sinensiumà morte vita functorum fieri solitum”,载Thomas-Ignatius Dunyn-Szpot,“Collectanea Historiae Sinensis ab anno 1641 ad annum 1700 ex variis documentis in Archivo Societatis existentibus excerpta, duobus tomis distincta”,(1700-1710): Tomus II, Pars IV, Cap. VII, n. 2(1685),第73r-v页。收入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104-105, I-II.
(15) 《临丧出殡仪式》(晚期抄本),《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47—465页。方括号内的小标题是作者所加,意在说明仪式指南严格遵循了《家礼》所载的仪式次序。各条规则的序号,为原文所有。
(16) 这一环节中没有提到《家礼》所载的沐浴和饭含。
(17) B13中的“本地之礼”,在文本C、D中都改作“粤中之礼”。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文中提到的风俗属于广东地区:文本B的封面上带有“大原堂”三个字(《临丧出殡仪式》[晚期抄本],《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48页),“大原堂”是当时耶稣会在广东的一座教堂。
(18) 对这种葬礼结构的概述,参看James L. Watson(1988a),“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James L. Watson, Evelyn S. Rawski(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12-15;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65-70.
(19) Ebrey(1991), p. 81, 84; Susan Naquin, “Funerals in North China: Uniformity and Variation,”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1988)39-40.其他抄本中没有提到过这些名称。
(20) 严谟:《李师条问》(约1694),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I[38/42]40/2;《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1,第115-216页。
(21) 也称作“大七”,参看郑小江:《中国死亡文化大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3页;陈怀桢:《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载《社会学界》第八卷(1934年6月号),第140页。可与Naquin(1988)相较,第41页。
(22) Watson(1988a), p. 7. 12. 18; Watson(1988b),“Funeral Specialists in Cantonese Society: Pollution, Performance, and Social Hierarchy,”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1988)133.
(23) Watson(1988b), pp. 118-119.
(24) Watson(1988b), p. 118.
(25) Watson(1988b), p. 122.
(26) Thomas D.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53、179、183、191.这部分因为世俗信徒比僧侣雇价低廉,该项习俗源于何时尚不可知。
(27) 这些是对白天(早晨、中午和傍晚)守灵的指导,与A7(B26)提到的夜间(傍晚、午夜和凌晨)守灵祷文不同。
(28) 关于这些祷文,参见Paul Brunner, L'Euchologe de la mission de Chine: Editio princeps et développements jusqu'ànos jours(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livres des prières), Münster(i. W.): 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64, p. 275.《天主经》与《圣母经》的念诵次数与《仁会会规》相同(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2,第476页)。
(29) 伏若望:《善终助功规例》(1638年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28页(入殓前念)、第431页(入殓后念)、第433页(安葬前念)、第434页(安葬后念);Lodovico Buglio利类思,《善终瘞茔礼典》(1675年后),第9a页(终后祷文);可与利类思译《圣事礼典》(1675)相比较,《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1,第489页。
(30) 关于《殓布经》,参看《圣殓布经》,载Brunner(1964),第111页。
(31) “四拜”而不是更常见的“三拜”,这在中国也相当普遍。《家礼》中提到过“四拜”(Ebrey(1991),第29、189页),在当时的许多著作,像徐乾学的《读礼通考》(1696),(影印四库全书第112-114册)中,也曾提及。
(32) 参看Eriberto P. Lozada, God Aboveground: Catholic Church, Postsocialist State, and Transnational Processe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150; Lozada对“小罗马”(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的一个村庄)的天主教葬礼进行了人类学描绘。他所观察到的葬礼,与17世纪同一省份的《临丧出殡仪式》中规定的葬礼程序惊人地相似。可对比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4-2005)》,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5-333页。书中有一段对磨盘山地区(湖北西北部)天主教丧葬礼仪的描绘,以及与《临丧出殡仪式》(晚期抄本)进行的对比。
(33) 可与传播儒家理念的丧葬组织所发挥的功能进行对比,见何淑宜:《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年,第209页。
(34) Brunner(1964),第184、278页;也见利类思编:《弥撒经典》,1670,卷末之《祝圣规仪》,第59a页。
(35) 按照Chen Gang的说法,“孝子”是对死者的儿子、女儿、义子、女婿、孙子、侄子、侄女和他(她)们的配偶、子女的泛称。见Chen Gang, Death Rituals in a Chinese Village: An Old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0) 80.
(36) Watson(1988b), p. 115.
(37) Watson(1988a), p. 4; Stuart E. Thompson, “Death, Food, and Fertility, ”载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1988), 第73页。关于Arnold Van Gennep对生命转换之礼的分析,参见Richard Huntington及Peter Metcalf, Celebrations of Death: The Anthropology of Mortuary Ritua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8页及其以下;Catherine Bell,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94页以下;Tong Chee-Kiong, Chinese Death Rituals in Singapore(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147.
(38) Watson(1988a),第10页。较为例外的一本关于葬礼的正确解释与信仰的著作,是Ferdinand Verbiest(南怀仁)的《天主教葬礼答问》,1682。
(39) 关于这个概念,参见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1903-1972),卷3,第429—479页:“Communion des saints”条。
(40) 对葬礼祷文,尤其是为那些身在炼狱者代祷的祷文的解释,见南怀仁《天主教丧礼答问》,第1a—2a页及其以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495—497页。这篇关于葬礼的文章,有时与南怀仁的《恶善报略说》(1670年撰),《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5,第509—530页合刊。
(41) Philippe Ariès, Images of Man Death, (Tran.) J. Lloy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9-147.
(42) “圣神相通功”涉及到信徒与圣徒问的品德交流。参见Alfonso Vagnone王丰肃编:《教要解略》,(1615),《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第203—204页;Brunner(1964),第275页。其他提到“通功”之处,尚有《圣母会规》(1673年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2,第456页;李九功:《证礼蒭议》(1681年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1,第104—105页。关于“通功单”,参见张先清:《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经卷在民间社会的流传》,收入《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4—142页。具体实例参看Maurice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Paris: Ernest Leroux, 1902—1912,第7441页收录的通功单(1740年印制);以及黄伯多禄(1783年6月10日以85岁亡故)和赵莫尼加(1783年7月9日以81岁亡故,这份通功单附在湖广总督报告天主教活动的一封奏疏[1784年10月31日]后面),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1页,编号421。
(43) 《圣教规程》(未署年代),Monumenta Serica 4(1939—1940),第472页。掩埋死尸的慈善工作,是许多组织的核心任务之一。参看《圣母会规》(1673年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2,第455页;《仁会会规》(未署年代),《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卷12,第475页。还有一些组织是专为照料临终者并组织葬礼而成立的,例如汤若望为反驳对天主教忽视葬礼的批评而在北京建立的圣会,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若望),Lettres et mémoires d'Adam Schall S. J.: Relation historique. Texte latin avec traduction franaise(Tianjin: Hautes Etudes, 1942)pp. 328-331. Fortunato Margiotti, “Congregazioni laiche gesuitiche della antica missione cinese,”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1963),第57-59页;以及1680年在澳门成立,后来传到大陆的“善终会”,Margiotti(1963),第54—57页。
(44) Cf. Lozada(2001), p. 12.
(45) Chen Gang(2000), p. 181. Marcel Granet,“Le langage de la douleur d'après le rituel funéraire de la Chine classique,”Journal de psychologie 15(1922): 105-106; Lozada(2001), p. 12, 150.
(46) C. K. Yang(杨庆堃),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35-38.(中文本《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7) Yang(1961), 第35页;Granet(1922), 第107-10页;Elizabeth L. Johnson,“Grieving for the Dead, Grieving for the Living: Funeral Laments of Hakka Women,”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1988)135-163; Huntington and Metcalf(1979),第23页及以下;Gary L. Ebersole,“The Function of Ritual Weeping Revisited: Affective Expression and Moral Discourse,”History of Religions 39.3(2000):238.
(48) 例如,Dapper曾在他的书中提到“哭泣与致哀;不间断的哭泣”(第374页),“哭泣”(第377页),“不断的哀声”(第381页),“他们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和哀泣比起来更像是嚎哭”(第382页),见Dapper(1670):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behelzende het tweede gezandschap...en het derde gezandschap aen Konchy, Tartarsche keizer van Sina en Oost-Tartarye: onder beleit van zijine Ed. Pieter van Hoorn. Beneffens een beschryving van geheel Sina... geschreven door Dr. O. Dapper. Amsterdam: Jacob van Meurs.
(49) 例如,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这样描绘南怀仁的葬礼:“天主教徒们一手拿着点亮的蜡烛,一手拿着手绢擦眼泪。异教徒们习惯于在这种庄严的场合里虚伪地流泪;但天主教徒的去世,使他们流下真诚的泪水”;见Louis Le Comte, Memoirs and Remarks...Made in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London: J. Hughs, 1737, p. 50.
(50) A2中的这种表达在文本B、C、D的相应条款中没有采用;B7中的表达在文本C、D的相应条款中没有采用。
(51) Yang(1961),第37页。
(52) 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33页及以下。在近代早期的西班牙,礼宴同样也是葬礼仪式的高潮;参见Carlos M. Eire, From Madrid to Purgatory: The Art and Craft of Dying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48.